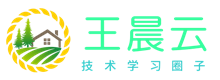2025年春节档的《封神第二部:战火西岐》(以下简称《封神2》)承载了观众对东方神话史诗的期待,却也在争议中暴露出续作难以回避的创作困局。作为《封神三部曲》的承上启下之作,影片在恢弘的战争场面与复杂的人性探讨之间摇摆,最终呈现出一部“高开低走”的争议之作。
一、视觉奇观与史诗框架的得与失
乌尔善导演在《封神2》中延续了前作对神话世界的建构野心。影片开场的“黄河浮桥截击战”以磅礴的调度与冷兵器碰撞的质感,展现了商周战争的残酷美学。十绝阵的布设更是全片高潮:闻太师以阵法召唤天灾,符咒与光影交织的视觉奇观,将封神宇宙的“神仙斗法”推向极致。三头六臂的殷郊法相尽管因特效质感被诟病为“廉价蓝精灵”,但其巨物压迫感仍具冲击力。
然而,特效的参差暴露了工业化体系的不足。雷震子的翅膀被批为“迪士尼廉价复刻”,通天教主的出场则因过度锐化的建模与西方魔幻风格“撞车”,削弱了东方神话的独特性。视觉盛宴与廉价感的并存,折射出中国视效工业在技术整合上的挣扎。
二、角色弧光的坍缩:从英雄到“恋爱脑”
影片试图以邓婵玉与姬发的双线成长为核心,却因叙事失衡导致角色崩塌。
**邓婵玉**本是全片最大亮点:戎装策马的飒爽、临危不惧的果决,塑造了一个反传统的女将军形象。那尔那茜的表演赋予角色冷峻与柔情的张力,尤其在浮桥战役中面对调戏歌声的从容,堪称女性力量的诗意表达。可惜后期剧情将其强行纳入“恋爱叙事”:与姬发的暧昧互动、篝火晚会的少女怀春、最终为爱牺牲的俗套结局,彻底消解了前期的独立人设。
**姬发**的塑造更显矛盾。作为三部曲的核心,他从第一部反抗纣王的觉醒者沦为优柔寡断的“道德标兵”。面对敌军主将邓婵玉的反复心软、十绝阵前的犹豫不决,与其说是“仁君”的复杂性,不如说是编剧对角色动机的失控。被动型人格与商业片主角所需的“行动力”背道而驰,导致观众难以共情。
三、叙事逻辑的硬伤与主题割裂
影片试图探讨“忠诚与正义”“成王败寇”等哲学命题,却因剧情漏洞频出而流于表面。商军明知浮桥有诈仍强行渡河、魔家四将降智追击雷震子、西岐军民在敌军压境时载歌载舞等情节,严重削弱战争叙事的严肃性。姜子牙的“钓鱼计谋”和姬发的“夜袭策略”缺乏智斗张力,更像是为推进剧情而设计的机械桥段。
更致命的是,影片在“神仙斗法”与“凡人战争”间摇摆不定。原著中杨戬、哪吒等仙人的法术沦为工具性辅助,而闻太师的法阵设定(如“时辰一到必死”的机械规则)缺乏神话的逻辑自洽。最终,观众期待的“封神宇宙”未能跳出俗套的“正邪对决”,反而陷入“大场面堆砌”的窠臼。
四、争议背后:东方神话改编的困境
《封神2》的口碑滑坡(豆瓣评分从7.7跌至6.1),折射出中国神话IP改编的深层矛盾:如何在商业类型片框架中平衡史诗叙事与观众预期?
乌尔善试图以《诗经》元素强化历史厚重感(如“伐木丁丁”的劳动号子、“适此乐土”的篝火吟唱),却因生硬的情感线冲淡了文化底蕴。对女性角色的“去污名化”初衷(如妲己从“红颜祸水”变为纣王的“痴情附庸”),反而陷入另一种刻板印象。
结语:神话重构的未竟之路
《封神2》并非全无价值。它对战争与人性的局部刻画(如闻太师的愚忠、百姓的生存挣扎)、视觉奇观的突破尝试,仍为中国神话电影提供了可鉴经验。但角色塑造的崩塌、叙事逻辑的断裂,也警示创作者:史诗的“形”易塑,“魂”难寻。若第三部仍沉迷于“工业糖精”而忽视故事内核,封神宇宙或将沦为又一场资本催生的视觉泡沫。